陳亨孝:老年成才的山鄉詩人
| 2018-05-11 10:12:13洪新瑜 蘇春鳳?來源:三明日報 責任編輯:蔡曉卿 我來說兩句 |
分享到:
|
陳亨孝在寫詩。
陳亨孝寫的書。
陳亨孝被采用的詩。 ●三明日報尤溪記者站 洪新瑜 蘇春鳳 文/圖 上學只上到初一;幾十年勞作、未碰筆墨;年近古稀開始學詩寫聯;10年前汶川地震時他寫詩作送到本報發表;6年前開始用律詩呈現四大名著,現在有3本付梓。 《感時悟事》《“三國”風韻》《“水滸”吟聲》《“西游”平仄》4本書,4000首現代四聲七律詩及1000多副對聯,都出自于一位80歲老人之手,而他初中一年級只上了一學期,曾經25年之間與筆墨無緣,68歲才開始學寫詩。這位老人叫陳亨孝,住在尤溪縣湯川鄉光明村。 近日,我們到湯川鄉拜訪老陳,老先生精神矍鑠,十分健談。 辛勞歲月難舍對文化的熱愛 陳亨孝生于1939年。他說,湯川鄉地處偏僻,當時戰火并沒有燒到那里,百姓的生活也相對平靜。陳亨孝和兩個哥哥都有上學,后來哥哥因父親去世,剛上初一就輟學回家,他也是初一時因病退學,那時他14歲。 當時,湯川鄉很多人會彈棉被和打棕衣。退學后,陳亨孝就跟著鄉里的老師傅學習這兩門手藝。“一次跟著師傅到縣里十三都打棉被,被三條惡犬撲咬,兩晝夜火燒般疼痛,險些喪命,也沒有藥可用。”陳亨孝說。一個星期后他恢復過來又跟著師傅東奔西跑。 他人高力氣大,學了一年就出師了。此后就跟老師傅合伙“四六開”,去福州等地打工,春季打棕衣,秋季彈棉被。他還到過清流縣,為鄉鎮供銷社彈棉被,文化館就在同一條街上,白天做完事情他就到文化館借書來看。“身上都是棉絮,文化館的人都知道我在附近彈棉被,都會把書借給我。”陳亨孝回憶道,他上半夜睡覺,下半夜看書,第二天就把看的部分講給一起彈棉被的人聽。 后來因身份問題,陳亨孝沒法在外打工,17歲起就回生產隊勞動。在丘山勞作時,當地慶豐收有迎龍燈的慶典,會請戲班子唱閩劇。他每天晚上都去聽,跟在隊伍后面,自己學著唱。戲班子留聲機里有幾片閩劇唱片,因為聽得懂福州話,五六個晚上下來,唱片里的每一出戲他都會唱。至今他還記得,當時最喜歡的一出戲是《荔枝換絳桃》。這期間,陳亨孝還學會了拉二胡,自學越劇。“拉二胡,我在湯川應該能排在前幾名。”老陳說。至今他家里放有3把二胡,閑暇時,他還會拉上兩首。后來他又喜歡上京劇,就跟著電腦學,還讓孩子買了唱戲機,用U盤下載了很多戲曲,插在機子里跟著學唱。現在他能唱40多首京劇,前些年還被鄉里推薦到縣里,參加“八閩秀才”選拔賽。 30年在生產隊勞作,陳亨孝寡言少語,很少動過筆。“中間有25年家里連一桿筆都沒有,偶爾幫別人寫信,總是囑咐別人要帶支筆來。”陳亨孝回憶道,后來,他到村棕床廠當了兩年管理人員,才再次拿起筆桿子。1987年,陳亨孝被抽到鄉企業站上班,這才經常與文字打交道。不過只干了兩年,他就回村了。 可以說,陳亨孝原先與“文學創作”沒有多少交集。 “生活到處都是詩” 陳亨孝與詩結緣,是在2006年。 “蔣昌雄、黃為艮兩位老師一直鼓勵我、引導我,可以說是連推帶拉硬把我引上文壇。”陳亨孝說,一開始他沒信心寫詩,覺得自己文化根底薄,連現代四聲都不會,怎么會寫詩? 蔣昌雄是陳亨孝的表侄子,一名村醫,工作之余他愛記日記、寫詩,日記寫了30年,寫詩20多年。 他不時教陳亨孝平仄、格式等基本知識。見陳亨孝不敢動筆,蔣昌雄寫了一首詩給他,并要求他必須回一首。在蔣昌雄的“逼迫”下,陳亨孝下功夫去學。他買來幼兒早教學拼音的掛圖,掛在床頭,每天除了吃飯、睡覺,就是學習,一個星期就學會了現代四聲。就這樣,陳亨孝用現代四聲寫下了第一首詩:《渺塵君贈詩·步其韻和謝》“承蒙厚愛見真情,把手施教字字金。佳作褒揚希望切,雅文鞭策寄情殷。初提筆硯手先抖,未扣詩門心就驚。愧謝栽培時恨晚,從茲近水必習勤。”蔣昌雄看了說:“這第一首詩是及格了,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” 此后,陳亨孝一發不可收拾寫起詩來,邊學邊寫。“我做夢都夢見自己在寫詩,怎么對仗,研究詞性。”他把自己的閱歷、家鄉的風物和趣聞軼事等寫成詩,還開始學寫對聯。 “想寫,生活到處都是詩。”生活就是他寫詩、寫對聯的素材和來源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,正身處三明的他看到新聞,百感交集,寫了《汶川地震亡靈祭》等4首詩抒發胸臆,并將手寫稿送到了三明日報社,沒想到被采用了,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:“民族苦難屢飛臨,五月西南天府傾。地震災生及蜀境,山搖命喪遍川丁。當頭大禍江河泣,滅頂奇兇日月驚。曠野哀鴻啼昊暗,瞬間顛晃地谷陵。” 詩作第一次發表,他備受鼓舞,開始積極投稿。建國六十周年之際,他的10首作品被收入《建國六十周年中國作家詩文大系》中,并榮獲“建國六十周年中國作家文學終身成就獎”;他的十八首新聲韻七律被《當代百家愛國詩詞精選》評為二等獎,被收錄到2009年《精選》第一卷中;他的對聯還被一家雕刻公司選中,刻在藝術品上…… 2011年,陳亨孝在《華夏詩聯書畫》上看到了一位收藏家籌建的藏書樓“六合書屋”向全國征聯,分為院門聯、藏書室聯、讀書室聯等8個門聯。陳亨孝揮毫潑墨,寫下8副對聯寄過去。沒想到全部被采用,還被評為“優秀征聯作者”,并給他寄來了整理后的書稿。“這是我最滿意的作品。”陳亨孝笑著說。之后,他還成為華夏詩聯書畫院詩聯類的研究員。 用詩寫四大名著 2011年,一個朋友從沙縣回來,給他帶了一本王力的《詩詞格律》,他如獲珍寶,細細研讀,并寫下了《感悟律詩格律與新舊聲韻的關系》的心得體會。沒想到,該文被刊登在《華夏詩聯書畫》的學術見解欄目上。 也是在2011年,陳亨孝將自己4年來寫的詩,選出1000首,匯編成第一本書——《感時悟事》。 從一個門外漢到自己寫詩出書,欣喜之余,陳亨孝也開始反思:自己寫了這么多的詩,意義在哪里?“孩子看了之后說我寫的太零碎了,很多都是些小事,沒什么大作用。”思慮再三,他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東西:把中國四大名著以現代四聲七律詩的方式呈現。 說干就干。2012年6月27日,翻開《三國演義》,陳亨孝寫下了第一首詩《楚漢相爭》。他根據書里每回的內容一邊看一邊寫,最多的一回寫了8首詩,少的只有一兩首。就這樣,他一門心思撲到四大名著里,每天寫詩,最多時一天寫了近20首詩。 老陳的床頭放著字典、成語詞典等工具書,有的已經翻爛了,用膠布粘著。他每天堅持寫詩,200多天寫成一本書,這樣的強度連年輕人都未必吃得消,而這位杖朝之年的老人卻做到了。這幾年他為四大名著寫了4000首詩。2013年7月,《“三國”風韻》付印;2016年初,《“水滸”吟聲》出版,并申請到了市里的內部書號;2017年夏,《“西游”平仄》印刷。2015年,他申請加入尤溪紫陽詩社,成為第100位社員。 現在,陳亨孝在準備為四大名著的最后一部書《紅樓夢》寫詩書,目前已寫了300多首詩。“出書難,現在出書的規定越來越嚴格,很難能印上書號。經費也緊張,對于我這樣毫無收入的農村老人家來說,每本書4000元還是一筆大數目。”陳老坦言,這幾本詩書能夠成功出版,都是自己四處奔走、自己出資,挺辛苦的。要是上級部門或愛心人士能給予支持和幫助,那他對完成《紅樓夢》詩書就更有信心了。 |
相關閱讀:
 |
 |
 |
打印 | 收藏 | 發給好友 【字號 大 中 小】 |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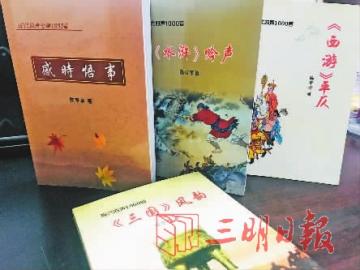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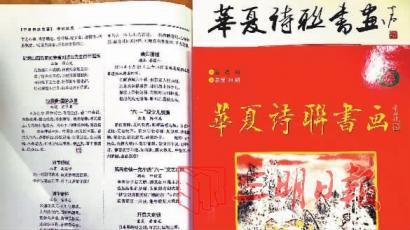

1ad7b80e-06dc-448a-9866-63a8b39c6595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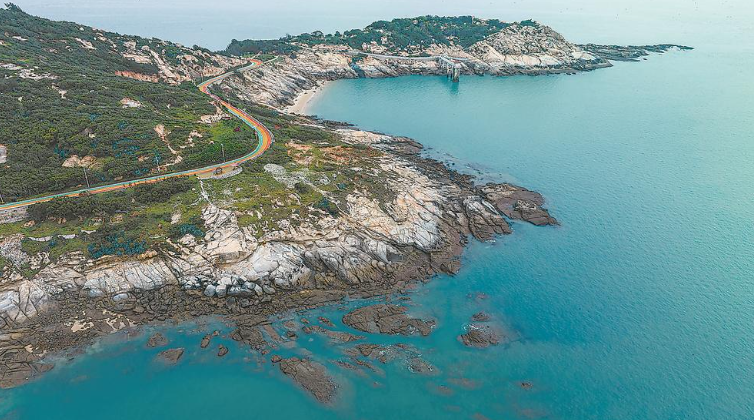
0d153859-bf45-4859-a6f4-9d7580f9af53.jpg)


